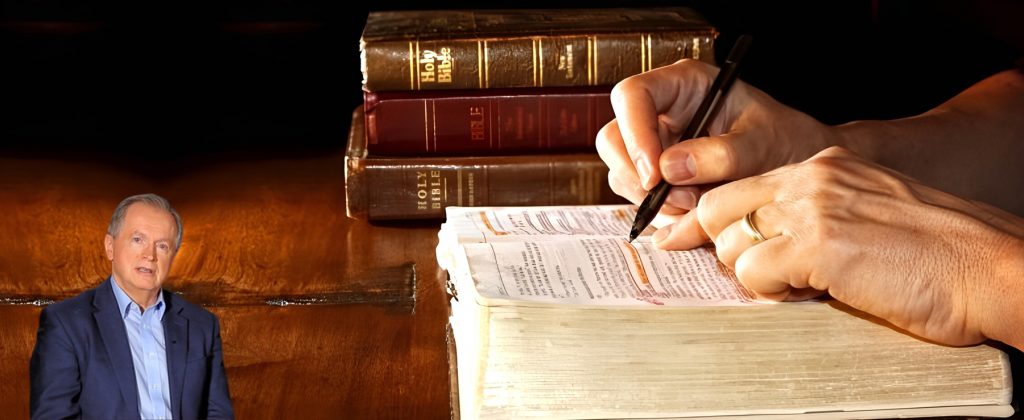01-1再思解经错谬之一
第一章:字汇研究上的错谬
文字何等奇妙!它既能传递信息,又能抒发情感,又是我们用以思考的工具。我们以命令的语言让事情得以成就,我们也以崇敬的语言敬拜神;同样的,语言也可能成为毁谤神的工具。
字汇是传道者的基本工具之一——不论是他所研究的字汇,或是用来解说他所研究的。可喜的是,现在坊间已有好些精湛的书籍,专门介绍字汇语意学,并经由这些书籍,一些滥用得到适切的提醒@1,而这些忠告都具有正面的意义。苏拿单(Nathan Söderblom)说得好:「语言学是针眼,藉由它,每只神学骆驼得以进入神学的天堂。」@2
我的要求并不高,只是希望能扼要地列出,一般传道者在从事圣经字汇研究时容易犯的错谬,并期望所列举的这些范例可以成为适切的鉴戒。
语意学上常见的错谬
1.字根的错谬(The root fallacy)
在所有的错谬中,解经者最常犯的错谬,就是假设每个字汇的意义与它的字形,或与它的构成有着密切的关联。由此观念导出的结论是:字汇的意义乃由语源学(etymology)来界定;也就是说,一个字汇的意义是由它的字根来决定的。我们岂不是常听闻,因为άπόστολος(使徒)的语根是άποστέλλω(我差遣),因此「使徒」的意思就是「被差遣的人」吗?在新英皇钦定本(NKJV)的序言中提到,μovoγενής(独特)的字面意义就是「独生子」@3;然而,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呢?又如:讲道者常以άγαπáω(爱)这个动词来比照φιλéω(中文也译作「爱」),并推论αγαπάω是一种特殊之爱,却没有提出更好的解释?
上述的推演都是荒诞不经的,至少在语源学上是如此。假使我们对英语的语源学知道更多一点,恐怕也会对英文的含义有同样多的揣测。田素顿(AnthonyC.Thiselton)就会以英文‘nice’为例,说明该字原是由拉丁文‘nescius’(无知)演变而来@4;英文中的「good-by」则是盎格鲁-撒克逊语「God be with you」(神与你同在)的缩写。当然,我们如今可以从历史追溯‘nescius’是如何衍生成为‘nice’的,「God be with you」简缩成「good-by」也很容易想象;但在今天,我从未见过一个说某人‘nice’的人,会以为此人在某种程度上是无知的,只因‘nice’的字根意义、隐藏意义,或者字面意义,代表的是「无知」。
语言学家鲁欧(J.P.Louw)就曾提出一个特殊的例子@5。在哥林多前书四章1节,保罗会这样描述自己、几法、亚波罗,以及其他领袖:「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ύπηρέτας),为神奥秘事的管家。」(NIV)而大约在一世纪以前,特仁慈(R.C.Trench)曾使以下这个观点大大流行:他认为ύπηρέτης是由动词έρέσσω(划)演变而来@6;因此,πηρéτης最根本的意思应该是「摇桨者」。特仁慈很快就断言ύπηρéτης原来就具有此义。罗拔信(A.T.Robertson)和霍富曼(J.B.Hofm-ann)更是推波助澜地认为,从语形来看,ύπηρéτηs是由ύπó和ξpéτηs结合而成@7,推论ξpéτης在荷马(Homer)著作中(公元前八世纪!),即是指摇桨者;于是霍富曼将此字和语形学(morphology)相联结,推断ύπηρετης基本上是「学摇桨的人」、「摇桨副手」或「附属的摇桨者」。特仁慈没有扯这么远,也没有说úπo有任何「从属」的含义。虽然如此,新约学者莫理斯(Leon Morris)仍推论ύπηρέτης为「卑微的奴仆」之意@8;巴克莱(William Barclay)更是指出ύπηρéτηs如同「罗马战船上最低层的摇桨者」@9。但这些看法仅依据一个可能的特例——而且它仅是可能,并非确定@10。在古典文学著作中,πηρετης从未用来指「摇桨者」,新约圣经中也没有这种用法。在新约用来指仆人的πηρéτηs,在语意上和下文出现的δáκovoς(执事),几乎没有差别。正如鲁欧所评析的,将úπηpéτηs的含义溯自ύπó和έpéτης,就像将butterfly(蝴蝶)说成是butter(奶油)和fly(飞)结合而成,或将pineapple(凤梨)说成是pine(松)和apple(苹果)的结合同样滑稽@11。
应用语源学探索字汇隐藏的意义,却把两个完全不同含义的字汇看成是同一个字源,将贻笑大方。巴雅各以希伯来文(lehem,面包)和(milhāmâ,战争)为例,作了特别说明:
在古典希伯来语中,此二字的字根对它们的语意到底有什么重要影响,值得怀疑。将这两个字联想在一起,是想象力太丰富使然,彷彿战争是为了面包的缘故,或将面包说成是战争必需品。某些语音相似的字汇,可能是因为谐音的缘故而并列,但这是一个特例,而且是可以清楚辨识的。@12
或许我该再回到早先提到的三个例子。άπóστολος(使徒)和απoστέλλω(我差遣)是否同源字,仍是有争议的。但在语意的讨论上,新约经文并不将意思集中于「被差遣的人」,而将重点放在「报信者」。通常,报信者是被差遣的,但报信者涵盖这个人所携带的信息,并且暗示他代表差他的那一位。换句话说,在新约里,άπóστολος通常用来表示「特殊的代表」或「特殊的报信者」,而非指「被差遣的某个人」。
μovoγεvης通常被视为由μóvoς(惟一;独一)加上γεvváω(生产的「生」)衍生而成「独生子」之意。在语源学上,γεv——的字根相当棘手:μovoγενής可以被简单地说成是由μóvoς加上γévoς(「类」或「族」)而成,意指「类中独一的」、「独特的」或类似说法。如果我们强调它的用法,便发现七十士译本将Tπ(yāhid)译作「单独」或「惟一」(例如:诗二十二20〔LXX,诗二十一21,NIV译作:「我宝贵的性命」或「我惟一的性命」〕;诗二十五16〔LXX,诗二十四16:「因我孤单贫困」〕),甚至连「生」的意味都没有。虽然μovoγενής在新约里,通常用来描述孩子和父母的血缘关系,但我们还是得谨慎界定其用法。希伯来书十一章17节称以撒是亚伯拉罕的μovoγενης(和合本译作「独生的儿子」),但明显其意不是「独生的儿子」,因亚伯拉罕也生了以实玛利,并且也和基土拉生了一群子孙(创二十五1~2)。然而,以撒确是亚伯拉罕「独特」的儿子,是他特别钟爱的@13。总而言之,像「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独一的儿子赐给他们······」(约三16,NIV)这样的译文,并不是为了白话文而改写,也不是要否认某一基要真理,而纯粹是为了语言学的理由。
同样,毋庸置疑的,άγαπáω(爱)和φιλéω(爱)二字的界定范畴虽不全然相仿,但此二字之间在语意上仍有重叠部分;但是,即使在意义上有重叠,若将此二字的语意诉诸字根,仍是错误的。举例而言,在撒母耳记下十三章(LXX),άγαπáω(动词)与同源字αyáπη(名词)皆能用来指暗嫩玷辱他同父异母的妹妹(撒下十三12~14);但当我们读到底马因贪爱现今邪恶的世界而离开保罗时,所用的动词也是άγαπáω(提后四10),这在语言学上并不意外。约翰福音三章35节用动词的άγαπáω叙述天父和其爱子的关系,五章20节再次重复相同的思想,却沿用φιλéω一字——意义上没有任何转变。因为对此二字所下的错误假设随处可见,所以我必须回过来重述我的重点:不论是动词的αγαπáω也好,名词的αyáπη也罢,这些字汇本身并不具任何内在性质,以提示我们有关它实际的语意、隐藏的语意,或某种特殊之爱。
针对上述的讨论,我要另外加上三项警告。首先,我并不主张每个字汇可以随便有任何的语意解释。通常我们可以观察出每个字汇限定的语意范围,然后根据前后文,在某种范围内修订或捏塑某个字汇的意义。但语意范围并不是恒常固定的,随着时间和用法的改变,语意也将相形变动。即便如此,我也没有说字汇的变动是没有限制的。我只是强调字汇的语意不能单靠字源来确认,甚至据此去假定某字根具有某种语意,而认定这语意会注入较晚期的字汇中。就语言学而论,语意并非字汇本身所具有的。「语意表明的是一种集合起来的关系,其中动词的表征只是一个记号」@14。从某方面而言,我们说「某字汇的意思如此如此」是合情合理的,但这只是在我们以归纳性的观察,提供字汇范围,或者特别指明在某段前后文中,某个字汇的含义。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过度倚赖语源学的包袱。
其次,一个字汇的意义可能反映出其组成部分的意思。例如,έκβάλλω这个动词是έκ加上βáλλω所组成,它的意思正是「我丢出」、「我掷出」、「我逐出」。一个字可以反映它的语源;我们得承认这样的情形泰半发生在综合性语言中,如希腊文或德语——因这两种语言的字汇和字义有显而易见的关系。但英语则较隐晦,它的字汇与字义间较没有自然而然的关系@15。即使是这样,我要阐述的是:我们仍旧不能假定语源和语意有必然的关系,我们只能依个别字汇,经由归纳后所发现的字汇意义来检视。
第三,我绝对没有暗示语源学的研究是无用的。语源学是重要的,例如在研究一些历时变化的字汇或在尝试指认其最原始的意义,甚至在研究同源语系,以及那些仅仅出现一次的字汇(hapax legomena)上,语源学功不可没。虽然在辨认字汇的语意上,语源学是相当有限的工具,但由于缺乏其他更有效的方法,有时就变得别无选择了。正如史尔瓦(Moisés Sil——va)在其卓越的研究中指出,语源学在旧约的重要性远胜过新约,因为在希伯来文里,仅出现一次的字汇非常多@16。史尔瓦说:「语源学的价值与该语言可供研究的资料数量成反比。」@17无论如何,纯粹以语源学作为载明字汇语意的基础,已经只能算是一种有学养的臆测而已。
2.语意时序的错置(Semantic anachronism)
这项错谬发生在我们将字汇晚期的用法,注入早期的著作时。这在相同语言中尤其容易发生,例如初代教父所使用的希腊文,就有别于新约作者所使用的,但有时不是那么明显;例如,当初代教父们使用επίσκοπος(主教)这词时,所指明的是监管许多地方教会的领袖,但在新约中却没有如此含义。
但是,当我们加上「语言会改变」这项要素时,这问题便呈现出另外的风貌。从英语‘dynamite’(炸药)来看,此字源自δúvαμις(dynamis,意指「能力」,甚至「奇迹」),我已经不记得有过多少回,听到传讲信息的人将罗马书一章16节翻译成:「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炸药』!」这错谬不仅是字根上的;更糟的是,这根本是顺倒语源学的举止——将现代的字义解读为新约时期的字义!这是将时序错置所导致的谬误。当保罗用δύvαμις时,他果真想到炸药吗?况且,就算是单独把「炸药」当成能力的类比,也是非常不恰当的。炸药会炸开东西,会毁坏东西,会爆裂岩石,可以凿洞——换句话说,它具有破坏力。至于保罗所提神的「能力」,常是指那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例如:弗一18~20);当它在我们身上发动,它的目的是使人「进入救恩」(είςσωτηρíαv,罗一16,KJV);它最终的目的是救赎,使我们得以整全完美。因此,除了语意上的时序错置以外,「炸药」不足以使耶稣从死里复活,或者使我们能够像祂的样式。当然,传信息者讲到「炸药」时,强调的乃是神伟大的能力。即使如此,保罗意指的绝不是炸药,而是空坟墓。同样的,在哥林多后书九章7节说到:「捐得乐意(cheerful)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乐意」在希腊文是ίλαpóv(「欢闹、狂欢」之意),若我们因此下结论,认为神所喜爱的是「引人发笑、逗趣滑稽」的人,或许下次教会在收奉献的时候,可以考虑将奉献袋摆在一张不断发出笑声的旋转唱片上。
时序错置的问题也出现在《今日基督教》(Christi——anity Today)期刊中,三篇和「血」有关的文章@18。这些作者试图以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血液奇妙的功用——特别是血液能排除细胞里的污物,并且为人体的每个环节带来营养。这些文章描绘了一幅何等美妙的图画:(我们被告知)耶稣的血洁净了我们所有的罪(约壹一7)。但事实上,圣经的含义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更严重的是,这种解释不仅变得神祕兮兮,并且在神学上有误导读者的嫌疑。「耶稣的血」这语词本是指耶稣遭受十分残暴、牺牲性命的死@19;一般而言,当圣经叙述藉由耶稣的血带来祝福时,其含义等同于藉着祂的死成就某件事(例如:称义,见罗三21~26,五6~9;或者:救赎,罗三24,弗一7,启五9)。当使徒约翰提及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时,他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盼望在于不断被洁净和赦免,而不是口里承认,行为却乖谬虚假(约壹一6可能是针对已具诺斯底派雏形的人士而发),并且持续地行在光明中,依靠基督在十架上所成全的救赎大功。
3.沿用过时的语意(Semantic obsolescence)
就某方面来说,这项错谬是上一项错谬的倒影,即诠释者赋予某个字语意,但其语意范围早已不存在;换言之,该语意早已过时。
我个人的书架上有一本《古英语辞典》(Dictionaryof Obsolete English)@20,当然,这当中许多字汇已失去了效用,而且早已被废置不用(例如,「to chaffer」便是一例,它的意思是「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但最棘手的还是那些仍被沿用却改换意义的字汇@21。在圣经语言中也有类似情况:例如,荷马时代的用字,早在七十士译本或新约作品中就已不复出现,这些古旧的字汇对圣经研究专家也已失去吸引力;希伯来文的字汇,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意义;古典希腊文中某字汇的意义,到了新约可以有其他意思。它们可能使粗心大意的解经者陷入目前这项错谬。
有些字义的变动是不难掌握的。时下英文字‘martyr’(殉道者)的语源是μáρτυς,若要追溯该希腊字的名词及其同源的动词,通常会有下列所说的几个发展阶段@22:
a.在法庭内(或外)提供证据者;
b.提供见证和确据者(例如:为自己的信仰作见证);
c.甚至在死亡的威胁下,仍旧见证其个人信念者;
d.以接受死亡来见证其信仰者;
e.为此原因而死者——殉道者。
当然,上述的发展阶段并不见得那么界线分明。在同一时期,μápτυς可以被某个人解释成其中一种意思,但却被另一个人解释成另一种意思;或者,同一个人对同一个字汇,因为上下文的不同而有不同的用法。在这个论据中,c阶段通常发生在法庭内,这使人联想到a阶段,因而构成该字汇在语意发展上的瓶颈。显然,在《坡旅甲殉道记》(Martyrdom of Polycarp)一章1节,以及十九章1节(主后二世纪中叶作品)完成时,e阶段已经隐约可见。标准古典希腊文辞典主张,当《启示录》写成时,e阶段已经形成:别迦摩教会并没有摒弃在基督里的信仰,「当我忠心的μápτuς(见证人?殉道者?)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启二13)后面的结论或许稍嫌过早:在启示录十一章7节论及两个见证人的叙述里,他们在被杀之前就已经完成了见证,这意味见证的意义不会超过上述的c阶段。因此,启示录二章13节中的μápτυς只是单纯的指「见证人」;或者,在约翰使用这字汇时,此字汇的语意范围包括了多重的阶段@23。
简而言之,字汇会随着时间缘故而变更其语意。现今,大部分人已警觉到「词尾」(diminutive suffixes)的功用,至新约书卷写成之际已大部分被扬弃;我们很难以年龄或身量区别ǒπαiς(小孩)和τoπαιδioν(孩童)。我们也察觉到许多「完成式词首」(perfec——tive prefixes)已失去部分或全部的功用。
从上述讨论看来,我们有必要质疑任何优先从古典希腊文,而非「通俗希腊文」用法切入,并据此界定新约字汇语意的解经进路。《今日基督教》月刊曾刊载米凯森夫妇(Berkeley and Alvera Mickelsen)讨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16节,有关以「头」为主题的文章。他们辩称「头」指的是「源头」或「源始」(sou——rce or origin)@24;但他们的诉求是依据古典希腊文辞典(LSJ,详细题目见本书之简写表),而不是新约及同时期的通俗希腊文辞典(此处指由W.Bauer所着的德文作品,时下简称BAGD。译注:BAGD中文本已由台湾浸宣出版社出版。此中文译本最多只能视为节译,因它删除了原书中所有和新约同时期的希腊文文献及出处)。按照新约希腊文辞典BAGD所列κεφαλη(头)的各项细目,并未明列「源头」、「源始」为其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