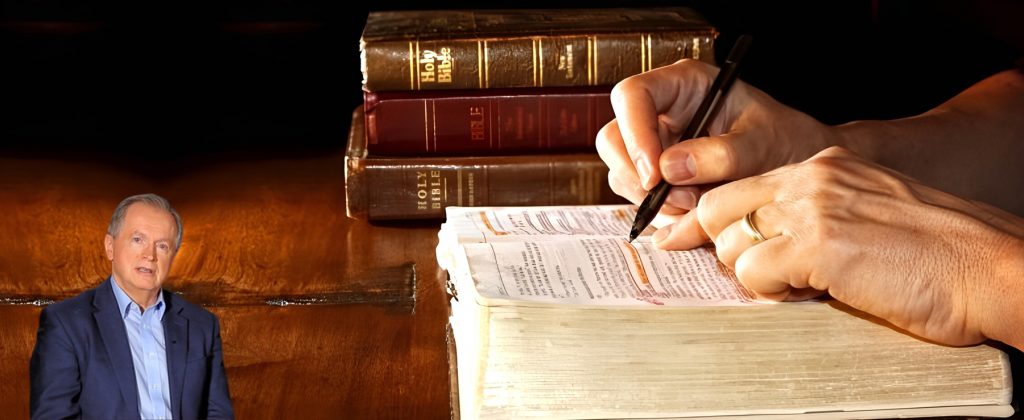00再思解经错谬
再思解经错谬
作者/卡森(D.A.Carson)
绪论
把焦点放在解经或是其他方面的错谬,乍听之下有点像讨罪:被点名批判者或许会心不甘情不愿地,稍微驻足检视自己所犯的错误,然而这个指出错谬的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就能造就人。当错误变得太普遍,而犯错者也未能意识到它的存在时,详细指出其中错谬,不仅具有鼓励作用,同时也诱导我们选取更好的解经方式。我期盼在论及解经上应该避免的错误时,我们能够变得更渴望正确解释神的话,若我把焦点太过集中在负面的引证上,目的只是希望你能从本书的正面引导得到益处。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先简述这个课题的重要性和危险性,并明白指出此课题研究的范围。
再思解经错谬的重要性
这个研究课题之所以重要,在于解经的错谬常常在我们中间发生——尤其发生在蒙神恩典,并肩负宣扬神话语重责大任的人当中。错误地解释莎士比亚的剧本,或分析错史宾瑟(Spenser)的某段诗体,并不会发生什么永恒性的效应;可是在解释圣经时,我们却不能容许类似的松懈或大意,我们处理的是关乎神的思想的作品,我们有必要下足工夫,为的是能确实地理解、讲解神的话。叫人惊叹的是,在所谓福音派的讲坛——圣经被公开尊崇的地方——常常发生歪曲正道的危险。当然,我们或多或少总会在解经上犯错:我也曾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缺失,但这要经过多少年更宽广的阅读,以及爱我的同事的指正,方能唤起我的留意。当一个传道者或教师充耳不闻自己在胡言瞎说,亦不警觉自己的言论如何摧残了神的教会时,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把矛头指向别人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先反求诸己。
批判性思考——一个被滥用的字眼——的精髓,在于提供证据。一个具批判性的解释需要就下列各项提出足够的证明理由:词汇、文法、文化、神学、历史、地理,或其他的项目@1。换言之,批判性的解经是为了能提供合理的抉择,以及充分说明何以某段经文必须作某种解释。批判性的解经反对追寻个人主观的臆测或高见,或盲目追随权威(诠释者或任何人所认为的解经偶像)独断的诠释和臆测的见解。这并不否认属灵的事情需要属灵的判断,或认为敬虔无关紧要;而是说,敬虔及有圣灵恩赐,并不能担保诠释不出错。当两位同样敬虔的诠释者导出完全不兼容的解释时,不仅不同意经文有多重意义者(关于这点稍后我会多作说明)@2不会接受,即便是最属灵的人,也不能说上述二者同时皆对。如果上述两位诠释者不但属灵,而且成熟,我们或可期望他们能平心静气地探讨,何以他们会有如此不同的结论。只要他们不断地谨慎研究、谦虚讨论,以及真诚地检验自己的见解,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他们能为互相冲突的见解找到解决之道。或许其中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或许两者都有某种程度上的对错,都需要被纠正;或许因没有定论,而无法解决这项释经上的问题。无论如何,从我们的观点看来,重点在于这两位诠释者是否真的投身于批判性的解经,并为其所达成的结论和观点,找到或提供支撑其见解的充足理由。
批判性的解经若能提供站得住脚的理由,我们就有必要学习拒绝无理、专断的解释。这就是这课题为何重要的原因。将解经的错谬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将成为更成熟的批判性解经者。
谨愼地处理圣经,能使我们更多「听」懂其中的圣言。我们都很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把在别处所领受到的传统解释读入圣经,甚至将我们的传统解释转化为圣经权威,几近偶像崇拜。然而,传统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而改头换面,不久之后,我们或许已经偏离神的话语;尤有甚者,我们还可能蒙昧地声称自己的神学观点是最合乎圣经、最正统的呢!事情若发展到如此田地,就说明我们没有好好地把圣经读懂,更不用说它是如何强化我们的错误了。如果我们坚信圣经的功能在于它不断更新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生活与我们所拥抱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必须竭尽所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聆听它,并且使用我们所知道的最好资源达此目的。
假使我们在意见分歧的解经课题上,希望谋求更一致的看法,这个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我对那些极尊崇圣经的人表白:对我们之间仍有那么多分歧的解释,我感到非常难过。当然,真理的崇高合一性是不容丝毫减损的,但事实上,那些相信正典六十六卷书乃神不折不扣话语的人之间,竟充斥着许多纷扰、不能兼容并蓄的神学观点。京斯顿(Robert K.Johnston)的看法是有道理的:
福音派的人皆声称自己拥有圣经的准则,但在许多关键课题上,却呈现神学陈述相互矛盾的窘态,暴露了当前他们在理解及诠释神学的本质上有问题。他们维护圣经的权威,却对圣经的教导无法达成一致的看法(即便同样是福音派背景的人),这是很难自圆其说的。@3
但京斯顿这番话显然也有未经斟酌之处:「很难自圆其说」指的是释经及解经方面,与圣经的权威并无关联。但他确实帮助我们正视目前解经上的混乱现象。
以下的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目前的乱象:为什么同样是非常尊崇圣经的人,有的人认为方言是灵洗的明确记号,有的人则认为说方言并非是强制性的?甚至,有些人认为方言这恩赐已经不存在了?为什么有所谓「时代主义」的看法?有的却持「盟约神学」的立论?何以加尔文主义有那么多的流派?何以亚米纽派、浸信派、重洗派又各自分了好些派系?为什么有些人在教会治理的理念上,捍卫长老治会的模式?有些人则强调会众制,或是主张自教父时期(或后使徒时代)起,就掌控了西方教会近一千五百年的神职阶级制度呢?容我大胆地质问:圣餐的意义是什么?关于末世论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见解?
当然,从某方面来看,这些理由不见得是理性的,也不见得会因为释义上得到改善,教派之间的歧见就会迎刃而解。许多褊狭的圣经教师和传道人,从来不会认真考量另一种诠释的可能;因为如果他们在讲经的时候,允许自己的问题受到全面挑战,他们将会失去心理上的安全感。他们不可能抛弃传统。但是,本书的对象并不是这些人。本书是为有智慧、够成熟、经过严谨训练,又在各个岗位上尽心尽力的虔诚领袖而写的:这些人岂不能在各种教义的歧异上,朝一致迈进吗?
当然,从表面上看来,我们有许多实际障碍亟须克服。有些教会领袖也许觉得他们没有时间花在这种高水平、待突破的研讨上;也许有些人认为其他人的想法已经根深蒂固无法改变,相喁对谈的收效不大一——他们觉得问题应该由对方提出,因为那些人理应承认自己的错误,改邪归正;有的人则可能碍于「身分」的缘故,觉得参与辩论过于冒险,会危及自己的地位。可是,如果排除这一切障碍,这些具有权威、不和的领袖,现在可能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中)谦卑地聚集在一起,寻求分裂的医治之道,并在导致他们教义分歧的课题上细论经文的意义,或讨论两段不同经文之间的关联。
开诚布公的辩论是可能的,或许一开始只是暴露各别见解的歧异,或是为这些歧异如何交织相连而纠缠不清。然而,一旦各派人马都能谦卑审愼地表述自己(宗派)在释义上的困难,剩下来的,只是解经及释经的辩论罢了。即使这些理论上的对手,最后基于解经证据不足,作出尚无定论的结语,双方还是能有所收获的。因为这是西方诚实面对难题的结果,任何一方都无法以圣经为据,来排斥对方。
长久以来,我经常置身于类似上述的辩论中;当然,某些时候是我主动出击。这类辩论有时候不太容易有什么进展:可能因为情感的包袱太沉重,或因为所需投入的时间过多。但是,只要建设性的对谈持续存在,双方就更能分辨出彼此论证的强弱、优劣。
从上述理由看来,研究解经的错谬就益发显得事关重大了。我们或许可以从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勉励得到一些激励。当保罗劝勉该教会要「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时,这勉励超越了仅是相互包容的范围,它也强调我们在神的圣言上必须学习迈向一致,并以神的思想为我们的思想。这当然也是我们尽心尽意爱神的一项操练。
像我们许多的神学观一样,我们的解经其来有自:我们的解经习惯得自师承,我们的老师又承袭他处。除非我们的师傅和我们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否则我们的解经工夫必定落伍。例如释经学、语言学、文学研究,或较复杂的文法研究和日新月异的计算机科技等,都在这时代联合成一股强大的趋势,要求我们在解释经文上有更多的自我批判。再加上一些已经波及我们基督徒范畴的发展(例如:新释经学对基督徒落实异地宣教的理解,就有很大的冲击);因此,成熟的思考是我们迫切需要的。在宗教改革时期,甚至上一个世纪,释经学并未臻至鼎盛地位,我们必须尽可能地向前辈(神学家)学习他们的精神;在面对本世纪最严苛的考验,怀旧或驼鸟心态,对解决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或转机)都无助益。
上述最后两项考量,提醒我正视费雪(D.H.Fis-cher)的观点,他对他的史学同仁曾严苛地说:
历史学家不仅需要为其本身的诠释发展出批判的测试准则,更要为如何达成此准则而建立测试······。在我的同事之中,有一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相信任何步骤都是可行的;只要时常发表的一些论述,不涉及任何重大错谬即可。现代编史学的乱象,正如士师记所记的以色列一般:「各人偏行己路,行各人眼中看为正的事;田里撒了盐巴,用小母牛耕种,全地都是饥荒。」@4
我不准备说解经学的景况会比上述编史学稳妥;但相同之处是无庸置疑的。
最后,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在于近三、四十年西方神学界的变化。前一代保守派所面临的对手认为,圣经其实是不足采信的,只有蒙昧无知的人才会信靠它。我们目前仍听得到相同的批判声;不过有更多声音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释经和解经两个层面上。有人认为保守派并没有好好把圣经读懂,他们硬将权威的概念加在圣经上,并在释经上牵强附会。对基要派攻击得最尖刻的要算是巴雅各(James Barr)了。巴雅各强调保守派人士并非真正明白圣经,认为他们使用的批判工具自相矛盾,甚至不诚实@5。在另一个层面上,甘德里(Robert H.Gundry)则在其近作《马太福音的文学及神学艺术》(Matthew: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中声称,他探讨圣经的方法要比传统保守派注释者更忠于圣经@6。类似上述的挑战真是俯拾皆是。
这样说来,传统护教的方法已不适用,且在释经和解经的竞技场上被远远地抛在后头。当务之急是重新检讨我们在释经及解经上使用的工具,严正地揭露各项迂腐或禁不起考验的论证——包括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缺失。
再思解经错谬的危险性
如果再思解经错谬的课题有其重要性,那么,它的危险性也不容忽视。
首要的危险就是:持续的否定论将危及灵命。当一个人以发现错谬作为他的终身职志时,他正向毁灭迈进。他第一个会丧失的美德就是:感恩的心;感谢神所赐予的美善事物,甚至相信在邪恶的事上仍有神的美旨和保守。第二个会丧失的美德则是谦逊;作为一个批评者,因为深深了解错误与乖谬的事(特别是别人的),难免心生骄傲。骄傲并非基督徒的美德,但持续地否定主义助长骄傲。我并不认为神学生(更不用说神学院的讲师了)能在此危险上免疫。
另一方面,对那些已经不太有把握,或自认传扬神全备圣旨既已重担压肩的人,类似的研究可能会使他们陷于更大的挫折里,甚至使之绝望。稍微敏感的学生也许会问:「假如解经存在着那么多陷阱,我怎么可能有把握自己对圣经的解释是正确的?我如何才能防止自己不教导错误?如何才能避免将基督不曾教导的谬理强加在祂的子民身上?或避免不删除重要真理的危险?因着我的无知和解经疏漏,将带给他人多少伤害呢?」
对这些学生,我只能回应说:假如你不勇敢迈出第一步,从事目前所论的研究,其所产生的错谬会比你遇到解经难题时才改善你的解经技术,犯下更多的错误。这其中最大的差异在于:进行研究将使你察觉长期以来所犯的错误。假如你真心关心你的事奉质量,而不光是为了自己心理上的安全感,选择逃避并非良策。无知也许带给人喜悦,但无知却不是美德。
进行批判性研究最基本的危险,在于它所形成的「距离」(distanciation)。但「距离」是批判性工作中的必要成分。「距离」叫人难熬,有时甚至要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我们可以从思想基督教神学院的一个实例,一瞥和「距离」有关的问题。
天恩在高中时代成为基督徒,上大学后攻读计算机;同时,他在教会竭力事奉,并在学生小组事奉上满有果效。他常常祷告,心里火热,除了偶尔的灵里饥渴外,他常在读经时感觉神亲自向他说话,虽然圣经有许多地方他不是很明白。他几乎已决定成为全职事奉者,当地教会十分肯定他的恩赐与呼召,他在深切感到不足的情况下,毅然踏上神学院的装备之路。
六个月之后,月换星移。天恩每天耗费多时背诵希腊文的时态变化,以及保罗第二次旅行布道的行程细节,也开始学习写解经报告;但等到他完成词汇研究、句型结构,以及各种综览和评析之后,神活泼的话语已不如往昔。为此他深受困扰,他感到祷告和作见证要比进神学院之前困难多了。他觉得非常纳闷:他并不认为神学院的老师有什么错,他们个个都相当虔诚,又有学问,且是成熟的信徒。
随着时光飞逝,天恩面临如下的抉择:他可以选择退缩到敬虔主义的角落,对索然无味的学识加以否定;或者,他可以选择卷进学术漩涡而失去真正的敬拜、见证,以及对圣经的默想;尤有甚者,他可以苟延残喘,期待毕业那日得到解脱,好让自己回到真实的世界。除了上述的选择,天恩有没有更好的路可走?难道这些都是神学生必经之路?
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会直截了当地说:「是的!」上述的体验对真正想要解经的人是必须的:这些都是「距离」感造成的。然而,理解「距离」的过程,却能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如何作出明智的回应。当我们尝试用批判的方式去理解圣经的内容(或是某人的思想)——选择据之以理,而不采取武断的模式,找出作者本意——我们就有必要先掌握作者和我们之间在经文上认知的距离。惟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与圣经本要我们了解的意思融合起来——惟有如此,我们的思想才会受圣经的思想所塑造,好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在融合之前,未能保持健康的距离,就没有所谓真正的融合可言:许多解经者所犯的毛病就是规避「距离」,自以为明白圣经,其实大部分时候,他是将自己主观的想法强加进经文里。
所以当神学院教导你运用批判性思考,你势必会面临困扰(却是对你有益)的「距离」。一所较差的学院不会有太多类似的困扰:因为校方只鼓励学生乖乖学习,而不鼓励审核学习内容。
经历「距离」是很辛苦的,且要付上许多代价。
但我必须再次强调,「距离」本身不是目的,「距离」的最终目标,在融合不同的见解。倘若解经的工作是随着「距离」感而得到滋养,这样的「距离」并非破坏性的。事实上,「距离」使基督徒的生命、信仰和思想更为健全壮硕,更具属灵的警觉性、识别力,且更合乎圣经,使人更具批判力。虽然在经历「距离」的过程中隐含着危险:对于努力整合基督徒生命和委身间关系的人,本书中的讨论会为你带来丰硕的收获;反之,放弃整合的努力,将可能导致你的信仰瓦解。
解经研究的范围
本研究并不是高等专门性的论述,它是为神学生,以及愿意严肃负起解释圣经责任之人而写的;对专业人士来说,此书并没有增补他们什么新知。
也许我应该补充的是本书何以命名为《再思解经错谬》(Exegetical Fallacies),而非「释经错谬」(Her-meneutical Fallacies),主要目的在实际操练。冒着过度简化之虞,我将如此区别二者:解经关注的是对经文实际的解释,而释经学的重点在诠释过程的究竟。解经以「本段经文的含义是······」作为终结;释经学在末了则以「本诠释过程包含下列的技巧和预设」为总结。二者显然有交集之处。然而,尽管释经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本身却不是目的,它是为解经而存有的。从某一方面来说,既然我讨论的是解释过程中各个角度的问题,自然也属于释经学的研究范畴。我的重点不在架设诠释过程的理论,而在解经者对圣经含义的解明;故此,我在本书的铺叙上偏重解经层面。
由于本书不是专门性的研究,故我未提供周详的参考书目。只有引用过(包括间接引用)的资料才被列入。
本书焦点放在解经上的错谬,而非历史性和神学性的错谬——除非后二者牵涉解经的范围,才会论及。
我不敢说本书所列出的各项错谬,是完整的清单,但所列出的项目都是我认为最常见的。
无论如何,我正竭尽所能对举出的实例保持公允的评析。我引用的错谬例子有来自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著述,有加尔文派也有亚米纽派的作品。其中包括市井无名之士和国际一流学者,我自己的两个解经错谬也在本书中接受了批判。大致说来,本书所列举的实例都源自相当重要的文献,而不是那些错误更多的大众化出版品,不过我也讨论了几位知名的传道人。本书取自福音派作者的例子最为繁多,这也反映本书出版的第一优先对象。
在本书中,我没有提到圣灵在解经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个旣重要、又不太容易拿捏的题目。若涉及此主题,则会使重心转移至释经学,这将有违本书作为实用者手册的初衷。
简言之,这是一本出自业余者之手的解经错谬手册。
附注
@1.关于「批判性」一词的用法,我参考Bernard Ramm,Protestant Biblical Interpretation:A Handbook of Hermeneutics for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2d ed.(Boston:Wilde,1956),101~103。此材料不见于同书之第三版。
@2.许多人常看不见此点。大约二十年前,我和一位弟兄同车,他告诉我那天早上灵修时,主如何教导他。当时他读的是钦定本(KJV)的马太福音。我发现不只他误解了钦定本的古老英文,事实上,钦定本的翻译,也偏离希腊原文甚远。我温和地提出我的见解,并综合指出这段经文的本意。这位弟兄却抗拒地说,圣灵从不说谎,圣灵亲自教导他的不会有误。当时我年轻胆大,也不肯轻易妥协,乃就文法、前后文和翻译问题,继续争辩。于是,这位弟兄搬出哥林多前书二章10节:「圣灵参透万事」,对我的解释不留任何商榷余地。于是我以齐人之道还治齐人,问他说,假如我提出的解释不是根据经文文法,也宣告这是主亲自教导的解释,那他将何言以对?他沉默了许久,然后作了这样的结论:「我想,只能说圣灵认为圣经针对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吧!」
@3.Robert K.Johnston,Evangelicals at an Impasse:Biblical Authority in Practice(Atlanta:John Knox,1979),vii-viii,
@4.David Hackett Fischer,Historians’Fallacies: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0),xix-xx.
@5.James Barr,Fundamentalism(London:SCM,1977).
@6.Robert H.Gundry,Matthew:A Commentary on His Literary and Theological Art(Grand Rapids:Eerdmans,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