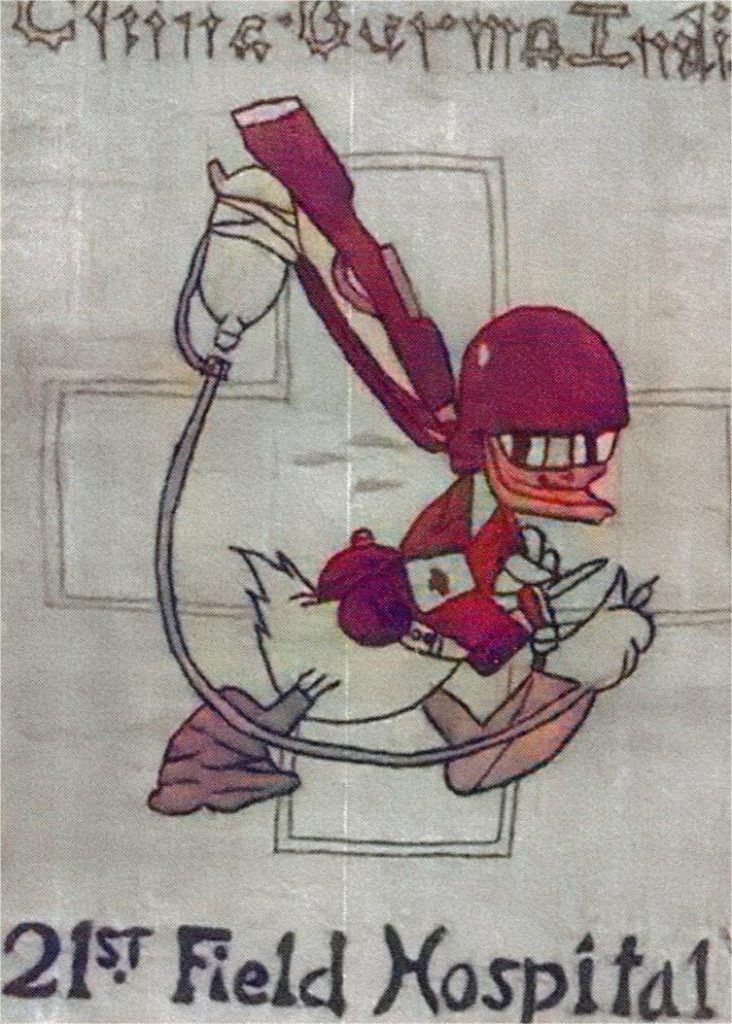19客旅
第十九章:回家的漫漫长路
安德森将吉普车停靠在了一个军事哨所,这个哨所位于我们前往的腾冲南部芒市,美军第21战地医院的路上。美国大兵拿出他们最好的东西招待我们,我们桌上摆满各种各样的美食:肉类、蔬菜、水果、甜点、沙拉还有奶油。在经历一年多的长期饥饿后,我和妈妈饱餐了一顿!吃过饭不久,我和妈妈的胃又胀又痛,异常难受。陪伴我们的战地医生突然醒悟是怎么回事,一边安慰我们,一边道歉说:是他疏忽了,对于我们的情况,应该少量进食,让胃慢慢适应。
在美军第21战地医院
芒市(又叫潞西)是一个不大的城镇。当我们来到芒市时,它看上去和大多数的傣族村寨没有什么两样。一棵巨大的榕树矗立在市中心,有好些人躺在树荫下,一边嚼着槟榔和酸橙一边在闲聊。嚼完的槟榔随口吐到地上,地上到处都是红斑点。市场上,有蔬菜摊、水果摊、肉摊,还有出售小猪的摊贩,小猪们的四只脚被绳子绑在一起,发出“唠、唠、唠”的尖叫声。
突然之间,战争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从没有发生过一样。在芒市郊外,美国陆军建立了一个战地医院——美军第21战地医院。医院规划得很整齐,沿着一条条马路搭了成排成排的帐篷。每个帐篷足够大,能容纳4张病床。由于还是雨季,天气潮湿阴冷,帐篷地板上铺上了竹垫子,房间里安装有木制的取暖器。每个房间都有电灯。
我和妈妈单独住一个病房。对我来说这就像到了天堂。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电灯。我对悬挂在帐篷中间的一根电线上闪亮的灯泡感到很好奇。木柴在火炉里面劈劈啪啪地作响。床上铺着白色的床单,摆放着干净、温暖的羊毛毯子。病房中还有一个架子,上面放着洗脸盆以及装满水的水壶。我和妈妈可以在病房里洗澡。
生活在一群对我们友善和关心的医生、护士中间,我感觉自己仿佛是在梦里。对我来说,天堂也不会比这更美!
在深山丛林里时,妈妈由于不想把我一个人抛在那样绝望、无助的环境里,她要活下去的愿望非常强烈。到了这里,她整个人一下子垮了下来。妈妈身上的疟疾、钩虫病和脚气,加上营养不良,让她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幸亏救援及时,要是美军晚到那么几天,妈妈很可能就没命了。
我们的病房变成了重症监护室,医护人员24小时照看着妈妈。吊针挂在床头,大剂量的维他命和抵抗疟疾的药被注射到妈妈体内。有时妈妈会清醒一会儿,我总能听见她低声对医生说:“请您一定照顾好我的女儿,请……”
整整一个月,妈妈享受着战地医院最好的治疗。
我和妈妈是1945年1月23日抵达美军第21战地医院的。圣诞节刚过不久,很多军人和医生跑来把家里寄给他们的圣诞礼物送给我。记得每天早上,我睁开眼,都会看到床头有一盒巧克力和一大堆甜点。尽管如此,只要听到飞机的引擎声,我就会没命地跑出去躲进附近树林中的大石头底下,或者跳进一个坑中、脸朝下趴着,用食指紧紧堵住自己的耳朵。
医院附近有一个美军军用机场,飞机不停地起飞、降落,美国大兵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从树林里把我找回来。
为了消除我内心的恐惧,美军从飞机场调来一名士兵,做我的“精神治疗师”,每天早上按时来病房帮助我。这是一个22岁的年轻人,名叫文森特·维佐(Vincent Vizzo),来自美国康州的布里季波特(Bridgeport)。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早晨,他开着吉普车带我来到飞机场附近的哨卡。他发现我的头发里有虱子,于是为我做了第一件事:从头上取下他的钢盔,装满热水,仔细地为我洗头发。
文森特是一个天然的心理学家。在给我洗完头后,他带我进入机场的控制塔,安排我和即将着陆的侦察机长对话。飞机着陆后,他带我上了飞机,让我看飞机上所有的设备,还让我坐上机长的椅子。文森特和机上的其他人都告诉我,这是美军的飞机,绝不会伤害我和妈妈,因此,我再也不用跑到树林里去躲藏了。
“路得,你现在再也不用再惧怕日本人了。有我们的保护,他们再也没法把你们带走!”文森特叔叔告诉我。
他牵着我的手,带我到一个防空洞前,那里摆了许多防空炮。文森特叔叔跳进洞里,举起他的手臂:“路得,快来!大胆点!往下跳!”我跳下去,落在他的怀里。他将我举起,把我放到炮身上,自己坐到我旁边炮手的位置上。他把我的右手放进他手里,我们一起把手放在大炮的操纵杆上。他告诉我:“路得,我们要拉动操纵杆了,这时大炮会发出非常大的嘈杂声,但你放心,它不会伤害到我们。”
“现在我们要开始射击了!”他沉着地告诉我。我坐在炮身上,没有办法逃跑,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我和文森特叔叔一起拉动了操纵杆:“嘣!嘣!嘣!”
防空炮发射了,但我还活着。
射击训练结束后,文森特送给我一只可爱的小狗乐迪(Lady)。我们住在美军第21战地医院的日子里,乐迪每天都和我在一起。
我相信一定是在梅杰·阿甘医生的指导下,文森特叔叔对我进行了针对性治疗,事实证明效果很好。
在医院里,我要帮助其他病人缠绷带。我还帮助制作药签,把医用纱布折叠成正方形作外科绷带用。我也常常去牙医诊所,在那里我看到许多以前爸爸使用过的相似的医疗器械,心里感觉很舒服。牙医别提有多么聪明,有一天他送给我一个他用面粉袋子做成的玩偶。
在他那里,我感觉自己都快要被宠坏了。
但在我内心深处,对日本人依然充满深深的恐惧和刻骨的仇恨。有一天,食堂的士兵哥哥要我和他们一起推着手推车去服侍生病的人。路上我发现一些受伤的日本俘虏被关押在一间重兵看守的屋子里。当我知道他们会吃到和其他病人同样好的食物时,我心里受不了了,我大喊大叫:“这些万恶的日本人!饿死他们!饿死他们!求求你们,不要给他们食物!”
离开战地医院之前,美军军官安排我带领一群美国士兵前往我爸爸埋葬的地方。到了那里,他们为爸爸重修了坟墓,在墓前竖起一个木制的十字架,还专门制作了一个铁制的铭牌,上面刻着爸爸的名字以及出生和死亡的日期。
他们以这种方式表达对妈妈和我的爱与尊重。
美国大兵给予我们的爱,我和妈妈终生感激。
来到保山
在战地医院住了一个月后,医生认为妈妈恢复得很不错,允许转院。一架军用飞机把我和妈妈接到保山,这次是英国大兵负责照看我们。在美国军人找到我们之前,他们就接到命令,要在中缅边界一带寻找“失踪的瑞典宣教士家庭”。
我们被安排住进中国内地会保山宣教站。宣教站里已经住了两位女宣教士。一位很年轻,身材很瘦,来自新西兰,名叫内蒂(Netty);另一个是在这里负责的,年纪要大一些,长得十分胖,来自苏格兰。因为某些原因,我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是我确实记得当她看到战地医院朋友们送给我的礼品、甜点和巧克力后,就把它们从我身边全部拿走,藏起来不给我吃。而我本来还计划留下一些,等回到瑞典时作为见面礼送给两个哥哥。
在战争中,一颗炸弹击中了宣教大院。有一栋房子被炸毁。院子的正中央也留下一个大洞。但在瓦砾和废墟中有一棵苹果树,粉红色的花朵正怒放着,在我看来,这预示着希望和未来。
春天到了!
妈妈仍卧床不起。我们被安排住进一楼的一个房间。房间光线很暗,唯一的光线来自门旁靠近顶棚附近的一扇小窗户,屋里也没有安装电灯。我们没有多少吃的。可怜的内蒂几乎每天都要哭上一次,她几乎从没有让自己吃饱过。每天饭菜还没有上桌,她的同伴就把食物差不多消灭光了。隔离和战争已经使她们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她们没有钱为自己买食物,当然更谈不上改善我们的生活,况且,我和妈妈也没有钱支付伙食和房租。
妈妈的身体又开始恶化了。
我记得那时是3月初,长在院子里炸弹坑旁边的苹果树正开着花。紫罗兰等植物在院子的各个角落里迎风生长。
“路得,快来看看这是什么!”是内蒂在叫我。她让我去看生长在石墙边上的一些的“神奇花朵”!
“我从未在这里种过这种花,但你不觉得它们很可爱吗?”内蒂问我。
50年后的1985年,我重返保山,并有幸看到内蒂和她的朋友们用生命和人们分享福音的工作的果效。又一次,有人介绍我看到一些“神奇花朵”:
一个欣欣向荣的基督教会!
当地的美军和英国军官正值休假,他们时不时会跑到宣教站看望我们。我记得有几个人来得很频繁:一位英国陆军少校,他的家在澳大利亚;还有一位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家都称呼他约翰逊(Johnson)先生。有一天,可能是因为发现妈妈的身体很不妙,我听到他们正悄悄地争论一旦妈妈过世,接下来由他们哪一个来照看我。
我既不想去澳大利亚,也不想去美国加州,于是跑下床大哭起来。
妈妈病得很重,脆弱到无法站起来。我心里充满了忧虑和恐惧。
和伍德一家在昆明
在保山住了一个月之后,我们搭乘一架美国军用飞机来到云南省会昆明,受到阿尔伯特·伍德(Albert and Nelly Wood)夫妇及两个养女的热烈欢迎。伍德夫妇是英国神召会的宣教士,很多年前他们一家来到梁河,成为我们家最亲密的朋友。
伍德伯伯一家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在去他们家的路上,他按捺不住看到我们的喜悦,并对爸爸遇害感到由衷的悲伤。他告诉我们,他曾前往中缅边界的英国军营,请求英军帮忙搜寻我们一家人的消息。
宣教站(AOG)位于昆明市中心报国路(Bao-Kuo-Kai)。这是一个典型中国建筑风格的四合院。屋子当中有一个砖砌的天井,有几间房子住着亚力克西·伯格和希格蕾·伯格夫妇(Alexis and Signe Berg)和他们的宣教队。这对夫妇和他们的宣教队都是战前由挪威的路德宣教会差派到中国宣教的。
亚力克西是爱沙尼亚伯爵的儿子,生下来就是贵族,大学时去英格兰学习医学。大学期间,他遇到一群基督徒朋友,于是奉献自己做了宣教士。他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发雷霆,要求他在信仰和继承权之间作出选择。亚力克西伯伯给父亲回了一封信、信中首先感谢他的父母给予他生命和关爱,但他已决心跟随耶稣,绝不回头,不论付上何种代价!
信发出后不久,他收到父亲的回信,宣布他已经失去继承权,而且从此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亚力克西伯伯选择了耶稣,从此被父亲赶出家门。但在耶稣基督里,他得到出奇的平安和喜乐。
耶稣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更宝贵!
在赫尔辛基(Helsinki)的一次基督徒医生聚会上,他遇到希格蕾阿姨,两人结为伴侣。后来,他们一起受到上帝的呼召到中国做宣教士和医生。他们在中国北部工作了很多年,由于战争的原因不得不南迁,最后来到昆明,和伍德一家人住在了一起。
由于战争的原因,他们在挪威和芬兰的朋友们中断了对他们的奉献,但他们在设在昆明的美国医院找到工作的机会。只要一有空闲,就跑到乡下给当地的村民提供义诊。
很快,亚力克西伯伯一家成了我们的好朋友。亚力克西伯伯为妈妈治好了脚气,也治好了我的疟疾。
上帝的供应真是充充满满!
亚力克西伯伯还让我想到了爸爸。每天他回到家,就会把我背在背上边走边说,有时坐在床边,用瑞典语和我聊天。亚力克西伯伯和希格蕾婶婶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那时,我不再担心妈妈会死,因为我相信即使妈妈死了,我还有养父母理解我、关心我、爱我。
尤其重要的是,我也爱他们。
在昆明,我度过自己10岁的生日。大人为我亲手做了一个蛋糕,还为我点上了蜡烛。这次生日聚会让我终生难忘!
参加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追思礼拜
德国路德宣教会在昆明市中心有一间教堂,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后,这里举办了一次追思礼拜。教堂的屋顶在二战期间被日本飞机炸毁,只有几堵厚石墙矗立在那里。教堂的木地板也在爆炸中烧毁,杂草从木地板被烧掉的一个个破洞当中欣欣向荣地长出来。教堂主人挑选出一些还能用的木地板,两头架起来用作教堂的长凳。
我和妈妈到的时候,太阳在明净的蓝天上闪耀着。德国牧师正在张罗着招呼客人,3个住在附近不远的女宣教士,一个牙医和两个护士正好走进教堂。她们每人穿一身白色长裙,肩上披着美丽的披肩,头上戴着帽子,脸上蒙着面纱。我觉得她们好美丽!我好羡慕!3个女士中的一位,卡洛琳·斯坦霍夫姊妹(Caroline Steinhof),经常跑到伍德的家里带上我出去玩。和她在一起,我总能吃到很多美味,玩得好开心。卡洛琳阿姨有一双神奇的眼睛,能从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情中找到欢乐。她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笑!
一些美军高级军官穿着笔挺的军装威风凛凛地步入教堂,坐到前面的长椅上,还有一张长凳坐满了美国女士,各种年龄都有,她们每个人头上都戴着一顶美丽的花边帽子。她们坐在一起,看上去就像一座美丽的花坛。
我和卡洛琳·斯坦霍夫阿姨坐在最后一排,好奇地观察这一盛大的场面。
妈妈坐在亚力克西伯伯和希格蕾婶婶之间。她穿着一件深蓝色的羊毛大衣,这是挪威的一位女宣教士送给她的礼物。妈妈头上也戴着一顶宽边礼帽,但帽子上没有像其他女士那样点缀花朵。由于没来得及买皮鞋,她脚蹬一双中国布鞋。由于脚气还未好,妈妈的脚依然肿得很大。
“感谢主,天气很美好!”遇见一个熟人,卡洛琳姊妹笑着给对方打招呼。
我在草丛中发现一只大蚱蜢,赶紧用手紧紧地捏住它。蚱蜢使劲咬我的手想逃脱,卡洛琳阿姨看着我,笑了笑没有说话。突然,蚱蜢猛地一跳,从我手里逃脱,跳到一位美军高官夫人帽子的正中央。
我害怕极了,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绝望中,我听到旁边的小伙伴们发出咯咯的笑声,然后感觉有一双手臂充满爱心地抱起了我。美丽的军官太太一边拥抱我,一边在我耳边低声说:“没关系,路得!你肯定也看到了,蚱蜢也喜爱鲜花!”
我大松了一口气,心里很感激她。
追思礼拜结束以后,我们和一对在战争期间从中国北部来到云南的瑞典宣教士夫妇见面,目前他们一家人住在中国内地会云南工作站。他们家有两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儿。
他们一家人即将前往印度。没想到,几个星期之后,我们两家人又在印度碰面了。
和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对话
在朋友帮助下,我们办妥了回祖国瑞典的护照。考虑到妈妈的身体状况,临行前,亚力克西伯伯写了一封信给加尔各答卡迈克尔医院的朋友,希望妈妈在开始漫长的海上旅程之前,再去医院接受治疗。
1945年5月19日,我们搭乘一架美军飞机离开昆明,机上只有我、妈妈和几个美军士兵。当飞机掠过中缅边境一带的高山峻岭时,飞行员走过来解开我的安全带,欢迎我进入驾驶舱。万里晴空下,高山峡谷和一望无际的密林尽收眼底,无数个村落零星地散落在这片美丽迷人的土地上。
“路得,就坐在这里!”飞行员指着他的座位对我说。等我坐下,他教我用双手紧紧握住前面一个半圆形的“轮子”。
“路得,你知道你手里握住的是什么?你已经成为一名飞行员了!”他笑着告诉我。
另一个飞行员叔叔也笑着说:“对!路得,你现在就在驾驶飞机!你可要紧紧握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命运现在可都在你的手中!”
离开时,他们在我胸前别了一枚美国空军的饰针,夸奖我:“路得,我们认为没有人会比你干得更棒!”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飞机降落密支那机场加油,然后直飞印度。靠近印度边界时,飞机遇到雷电和暴雨。深夜时分,我们平安抵达加尔各答机场。
瑞典领事馆派专人来机场接我们。他开车把我和妈妈送到一个美丽的水上俱乐部,俱乐部位于一处人工湖旁,是专门为撤离中国的宣教士租赁的。我们到时,已经有19名瑞典宣教士和4个小孩住在这里。准备和来自美国、英国的宣教士们一起回国。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罗伯特·汤普森博士(Dr.RobertE.Thompsin)正在和孟加拉当地官员密切联系,一旦安排好行程,住在这里的瑞典、美国、英国等西方宣教士就立即启程回国。
按照规定,男人住一楼,女士和孩子住二楼。由于床位不够,许多人只好睡在地板上。一楼男人们睡觉的地方,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要卷起铺盖,当餐厅用。但我没有听到一个人抱怨。
妈妈上楼依然很困难。好不容易上了楼,却没有床铺。妈妈精疲力竭,瘫倒在一张椅子上。这时,一位高大、苗条的女士走近我们,自我介绍说:“嗨!我名叫赫勒娜·埃里克松(Helena Eriksson),是瑞典路德宣教会派驻印度的一位宣教医生。”一名医生!上帝在这里给妈妈预备了她的专用私人医生!
感谢主,赫勒娜把她的床让给妈妈,而她自己,则靠着她的皮箱睡觉。
两天后,卡迈克尔医院邀请妈妈前往接受治疗。住院后,第一个来探访我们的是瑞典领事馆的一名职员,她给我们带来瑞典亲友寄来的信和报纸。经历几年的与世隔绝,我们终于收到家乡亲人的来信。妈妈因为手指已经完全失去知觉,就口述一封信让我写好,寄回家乡。
那时我只有10岁,很快就不耐烦整天坐在病床上画画的生活。而且我总是好奇地问来问去,弄得医生、护士很不耐烦。于是他们允许我去外面玩耍。
妈妈旁边的床上,躺着一位女士,大家都称呼她末底改太太。她病得很重。在我小小的心灵里,我确信她一定是《圣经》中以斯帖王后的一个亲戚,因为王后的叔叔也叫末底改。我常常溜到她那里问她问题。但是令我失望的是,她病得太重了,根本没法说话。
于是,我经常跑到医院的阳台上,站在那里,看着路人做白日梦。当有人从楼下经过,我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向一些人吐唾沫。我的恶作剧被护士姐姐发现了,我犟嘴说:“我从来没有向穷人或者中国人身上吐唾沫!”
这是事实。我只挑选那些穿着皮大衣的时髦女郎吐唾沫。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昆明时,有一次,亚力克西伯伯看见我靠在窗户边上正向马路上的一个垃圾桶吐痰。他问我:“路得,亲爱的,我相信你没有向一个可怜的中国人吐痰,是吗?”这句话让我感到很羞愧!
一天,我们听到一个声名显赫的人,英国派驻缅印的最高长官蒙巴顿勋爵,即将来医院探访我们。
蒙巴顿勋爵!印度的总督!他一定是一位大君,会骑着一头装饰得很美丽的大象来看我们。
他看上去一定是一个印度王子!穿着金色的锦缎长衣,头上裹着白色的头巾,前额处镶嵌着一颗大大的红宝石,周身镶嵌数不清的宝石,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是多么渴望我心中的王子快点到来啊,护士姐姐们看上去也和我一样激动。蒙巴顿勋爵要来的那一天,她们要求所有的病人都躺在床上。我的床罩被紧紧地固定起来,我感觉脚很不舒服。刚想动一下,护士姐姐就跑过来:
“不要动!”她对我说。
护士姐姐们每人都在自己白色的长裙外面,斜挎一条红丝带。从门口一直到病房里,她们排成了一排,笔挺地站立在那里。
突然听到一声大喊:“勋爵到!”我看见院长和医生陪着一名高大纤瘦的英国人走进来。这个英国人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卡其色军服。
排成一排的护士姐姐们不约而同地向这个普通的英国人鞠躬。
一定是什么地方弄错了!这不可能是勋爵!很可能只是为他打前站的守卫。
就在这时,这群人来到妈妈的病床边。医生把妈妈介绍给那个男人。
“啊,是的。我早已听说过她们的事情。”穿着卡其色军服的男人说。他开始亲切地问妈妈一些问题。离开时,他把头转向我,用手轻轻拍拍我的脑袋,说:“小朋友,战争是多么悲哀和可怕啊,我盼望你再也不要经历这样的灾难了!”
我还沉浸在对白马王子的想象中,眼前发生的这一切让我很失望。我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我看见站在这位探访者后面的姐姐们用表情示意我安静。这反而激起了我说话的勇气:
“先生,你的大象在哪儿?”
“我的大象?”他有些吃惊,笑着看着我:“小朋友,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先生,我本来以为你一定会骑着一头白色的、装饰得好漂亮、好漂亮的大象,就像一个真正的印度大君或者国王那样,威风凛凛地来呢!”
蒙巴顿勋爵哈哈大笑:“所以,亲爱的小朋友,我一定让你失望了,”他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发:“的确,我是印度的总督。但小朋友,我还是一名在缅甸和日本人打了很多年仗的士兵啊!我得到了关于你们一家的报告,衷心地盼望你们万事如意。对了,你的问题还让我想起我的两个小侄女,丽兹和玛格丽特·罗斯,我告诉你,她们现在已经回到英国了!”
公主?我也有!我有用纸做成的公主玩偶,现在还放在我幕水的家中!而现在,公主的亲戚蒙巴顿勋爵亲自来医院探访我和妈妈!
他不是从故事书里面走出来的王子,却是一名高大普通的士兵,穿着卡其色军服,有着一双友好、慈爱的灰蓝色眼睛。他告诉我,他讨厌战争。
护士姐姐和在场的医生们没有一个人因为我和蒙巴顿勋爵的对话而责备我,尽管这肯定不是皇室拜访时的外交礼仪!
从印度到里斯本
一天,我们收到瑞典领事馆的一封来信,信上说:已经在一艘葡萄牙邮轮里给我和妈妈预定好了舱位,从印度西海岸果阿前往里斯本,我们可以立即搭乘火车去孟买。
路上,我一直把一个小包小心地挂在我的脖子上,里面装着船票、护照、药品和现金。由于妈妈的手指仍然没有知觉,验票、买东西等都由我包了下来。妈妈走路很吃力,医生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她出院,结果还是妈妈签署了一份责任自负的文书后才被允许离开医院。
在车站,我们发现犯了一个错误,我们订的是二等舱。但没过一会儿,一个乘警前来把我和妈妈请到一等舱去住。幸运的还有,隔壁的包厢里住着我们在罗斯福总统追思礼拜上遇到的来自瑞典宣教会的宣教士卡尔·约翰(Karl-Johan)、爱尔丝夫妇(Elsie Bergquist),和他们女儿贡沃尔(Gunvor)和安妮(Anne-Marie)。
到了孟买,我们和大卫叔叔、朱迪思阿姨在一起呆了一个星期,还遇到瑞典宣教会的埃尔静(Erjen)、奥尔加(OlgaNewman)夫妇以及他们的小女儿古丽娜(Gunilla)。他们一家来自中国北方,在罗斯福总统的追思礼拜上我和他们家也见过面。埃尔静叔叔一家将和我们乘同一艘轮船回国。
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钱,瑞典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帮我们垫付了船票和妈妈在加尔各答的医疗费,妈妈承诺在回到瑞典后如数归还。
感谢主!在果阿,我们又遇见赫勒娜医生!她看见妈妈很虚弱、很忧虑,对她说:“上帝专门派我来做你的私人医生!哈拿,整个旅程你再也用不着担心了!”
赫勒娜医生很贴心地跑到商场买回一个专供船长休息用的舒适的躺椅,在海上旅行期间,妈妈每天都躺在这个躺椅上休息。这张充满爱心的椅子现在还珍藏在我的家中。
我和几个孩子每天跑到沙滩上戏耍,在飞机库旁边的山坡上的一条小溪里栋各种漂亮的贝壳。玩得开心极了!
我们搭乘上自二战爆发之后,第一艘从印度开往欧洲的平民轮船“殖民号”,船上差不多有1000名乘客。由于苏伊士运河依然封航,我们得绕过南非航行很长的路。在船上,我和妈妈与两位年长的瑞典女士共用一个一等船舱。
我随身携带一小口袋贝壳上船,许多贝壳里面的生物还活着。我小心地把这些宝贝藏在我的床底下。没过几天,我们的船舱便充满了一股臭味。清洁工跑来检查,结果发现臭味来自我放在床下的那袋宝贝。我又哭又闹,央求留下它们。幸亏遇上一个好心的船员,他帮我清理了这些贝壳,并把它们放到一个通风的地方。
贡沃尔和安妮整天和我一起玩,他们的爸爸召集船上的瑞典人一起做礼拜。我们每天都有晨祷。吃完早饭,女宣教士英格堡·阿克塞尔(Ingeborg Ackzell)就把我们这些小孩召集在一起学习瑞典语。她还要求我们每天记日记。
8月29日,我们抵达葡萄牙的里斯本。
终于回家了
由于没有办好签证,无法搭乘火车穿越欧洲大陆,我和妈妈,还有赫勒娜医生,在里斯本等了整整一个月,终于搭乘上瑞典劳埃德航海公司的突尼斯号前往瑞典的哥德堡。旅途中,我们还遇到一位从利比亚回国的宣教士希尔达·马特松。
突尼斯号在葡萄牙北部的波尔图港装载生产葡萄酒用的软木塞后,航行到了爱尔兰海。为了避免触礁,船只绕过英吉利海峡。
穿过克莱德河,轮船抵达格拉斯哥。继续往前穿过佛斯和克莱德运河。
驶进北海,瑞典就在不远的前方。不知道什么事情,所有乘客被船员紧急叫上甲板。这时太阳已经下山,我们看见一股黑色的浓烟从突尼斯号的货仓中喷涌出来。原来是堆放在货仓里的软木塞发生了自燃。船长发电报给哥德堡请求援助。不久,一艘救难船慢慢驶近突尼斯号,我和旁边的孩子们都向救难船上的船员不停地挥手。船长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情况需要,所有乘客就立即转移到救难船上去。
瑞典的海岸线就在我们眼前。我听到身边有人说:
“快看、这就是瑞典的海岸线!”
“在哪里?在哪里?”周围的人齐声问道。
“看那边!看那些灯光!灯光就是!”
那是从温加港(Vinge)外的灯塔上发出来的光!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瑞典简直就是天堂!而天堂里没有黑暗,处处充满了阳光!但这里怎么会只有一缕光呢?船慢慢驶近海岸,我看到越来越多的灯光在漆黑的夜空中闪烁。
这时是10月,我看见大海、海岸线完全被浓雾笼罩着,除了几处灯光外,一片漆黑!
这和我心目中的天堂差距多么大啊!
突尼斯号缓慢地驶进港口,抵达指定的码头。消防队员早已严阵以待,泊绳一拴牢,他们就拉着水管跑到甲板上。
妈妈站在船栏边,焦急地注视着不远处的码头。她的衣着和在昆明时一模一样,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护士大衣,戴着黑色宽边的帽子。她站在那里显得多么瘦啊!
我穿了一件褐绿色的保暖外套,是用美军羊毛毯子改制而成的。
天气很冷。我把在葡萄牙时别人送我的一顶贝雷帽使劲往下拉,盖住我的耳朵。
突然,我听到妈妈大喊起来:“大卫!撒母耳!他们在那!路得快看!孩子们!孩子们!他们在那!天啊!他们都长这么高了!”
我望向码头上一堆穿着冬衣的人,发现里面站着两个穿着灰色防水大衣的青少年。
“他们是我的哥哥吗?”我想。
突然,我被一个高大强壮的消防员抱了起来。
“小姑娘,你一定盼望快点离开!”他抱着我走下跳板,把我放到码头上。另有一个消防员扶着妈妈走下轮船。
接下来的一幕是热情的拥抱和欢乐的泪水!
在甲板上站了这么长时间后,我和妈妈都饥寒交迫。朋友们把我们带到一家夜餐店。听到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说瑞典语,我感到很新奇。我坐在两位哥哥,14岁的大卫和15岁的撒母耳旁边。我离开瑞典时只有几个月,从来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过。我们在信中给彼此画过画,但战争割断了我们所有的联系。
我们聚在一家餐馆里,环绕在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四周。除了惊讶,留给我的还是惊讶!有人为我们小孩点了牛奶,约翰逊牧师热情地大声嚷道:“请为小路得要一大杯牛奶!”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喝到新鲜牛奶了,而且是这么大的一杯!妈妈用眼睛示意,即使不喜欢这个味道,也要一口喝完。
我深吸一口气,端起玻璃杯一口喝完。虽然我不喜欢牛奶的味道,但还是喝得一滴不剩。我刚松了一口气,就听到约翰逊牧师在说:“你们看,路得多么喜欢牛奶啊!真是太可怜了!我相信她一定有好多年没有看到牛奶了。服务员,麻烦你再给她一杯!”
这就是我回到瑞典的第一印象,陌生的国家,陌生的人民。
我下定决心,要慢慢地了解我的两个哥哥,也希望在这个不熟悉的环境里面得到他们的爱护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