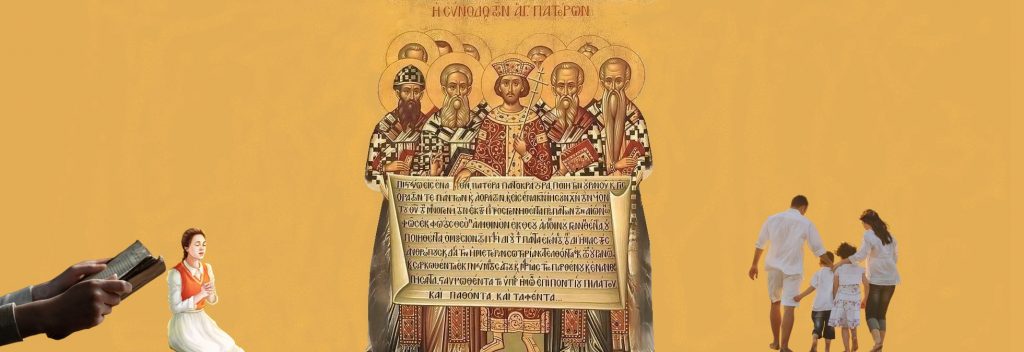01信仰与信经
信仰与信经
阿里斯特-麦格里斯(著)
第1章、旅途:发现宇宙意义的线索
我曾与几个学生朋友骑自行车环游法国。有一天,天气格外炎热,我们决定在乡村路旁休息一会儿。我正从路旁的水泵接水,发现有一人沿着这条路轻快地走来,双臂如走军姿般左右摆动。
他注意到水泵便停了下来,等着我接完水。我礼貌地询问他往哪里去。“哪儿也不去!”他回答说。他说散步只是他从生命的虚空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我哪儿也不去,只是在消磨时间罢了。”说完后他继续往前走。我看着他目空一切地大步踏向远方,在没有特殊目的的旅途上,高昂着头。
人生就是一次旅行。无论你是否相信上帝,人生原本如此。我们正沿着一条神秘的道路旅行,思索如何才能使其有意义。它通往某个重要的地方吗?它真的通往任何地方吗?在旅途中,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从文明诞生之日起,许多作家就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归根结底,我认为只能有两种答案。
第一种,让我们来谈谈法国无神论哲学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20世纪60年代,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流光溢彩的青少年(bright young things),他确信生命的意义就是毫无意义。他认为一切存在都“没有理由,延长寿命出于软弱,而死亡则出于偶然”。一切存在既无方向也无意义。“我们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为了维持生命而吃吃喝喝,但其实都是虚无,没有活着的理由。”
我在法国遇见的那位陌生人大概会对这样的观点产生共鸣。全世界最著名的无神论者、《上帝错觉》(The God Delusion)一书的作者、“新无神论”(New Atheism)的创始人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1941-)也持有相同观点。他宣称:“在宇宙的中心,没有设计,没有目的,没有善恶,只有盲目无情的冷漠。”除了繁殖我们的基因外,我们没有任何活下去的理由。我们正沿着一条不通往任何地方的道路前行。
这种冥顽的无神论思想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存在上帝,不存在超自然的领域,也不存在赋予万物意义的“宏大故事”(big story)。但它何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相信上帝呢?道金斯的回答简单而武断:有信仰的人都被迷惑了。他们是一群固执己见的人,无法面对宇宙的惨淡与毫无意义这一残酷现实,只能借助虚构的意义来自我安慰。
我以前也这样想。我认为聪明人都知道上帝不存在,生命没有意义也没有目的,傻瓜才不这样相信。能挤进知识分子与文化精英之列让我自我感觉良好。尽管这听起来十分傲慢且自以为是,但我却因蔑视身边相信上帝的人并标榜自己比他们更聪明而自得其乐。
我最鲜活的校园回忆之一是夜晚透过宿舍的窗户仰望星空。天晴时,我可以看到繁星就像黑天鹅绒上明亮的光点。我虽然时常被夜空纯粹的美所征服,但内心幽暗的思绪却使我分心。宇宙的浩瀚似乎在强调人自身的渺小。在这个宏伟的布景下,我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什么都不是。
然而,还有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或许宇宙中布满发现其意义的线索;或许这些线索可以引导人们发现事物更深层的秩序并找到自己的位置。我后来信服的这种观点强调现实的真正意义是认识上帝。一旦我们领会到这一点,人生便充满意义。“全景”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事实上,这个世界充斥着上帝存在的暗示和迹象,以至于无神论者只有闭上眼睛才能给自己的不信找个借口!
我们很快将讨论现实的“全景”这一核心主题。不过眼下,让我们先来探讨一下“信仰”的真正地位。
什么是信仰?
对于慷慨激昂的无神论者来说,“信仰”好比公牛眼前的红布。所有信仰都是迷信!新闻媒体人克里斯托弗-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1949-2011)在他生命最后的几年里成为无神论的主要辩护者,他大胆宣称:“我们的信仰根本不算是信仰。”“换句话说,希钦斯只能接受可以被证实的事物。在他看来,宗教人士逃避现实,拒绝为其信仰提供任何形式的理智辩护,而科学和逻辑都已证明了无神论者的想法。
这种“信条”简洁明了。但它是否正确?能否经得起考验?希钦斯的许多批评者指出,他的作品充满无法被证实的论断,尤其是涉及道德与宗教信仰的话题时。毫无疑问,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但他许多大胆的言论没有任何证据作支撑,理查德-道金斯的作品亦是如此。文化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1943-)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道金斯活着更多倚靠的是信心而非理性。”
希钦斯认为,数学和逻辑这两门学科可以证明事物是否正确。这一点无人否认。下面的陈述是完全可靠和可信的:
2+2=4
整体大于部分。
可悲的是,生活的很多方面却无法证明。我们当然可以给出很好的理由相信比如强奸是错的、民主比法西斯主义更好等等,但它们本身无法得到证明。
那么,逻辑和数学的真理又有多么重要?难道一个徘徊在自杀边缘的人,在得知“整体大于部分”之后会放下手中的左轮手枪?或在得知2+2=4后倒掉手中的氤化物?这些陈述或许千真万确,但其对于人的生存意义而言并不重要,因为它们无益于人类心灵深处的疑问和渴望。
我可以证明2+2=4,但我无法证明生命是有意义的。我也无法证明19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M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主旨——“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我同样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我当然可以给出一些很好的理由去相信这些信念是正确的,但我们当中任何人都无法证明这些信念本身是正确的。只有浅显的真理可以被证明,而人生最深邃的真理则超出了终极证明的范围。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没有任何人——无论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可以证明我们生命中赖以存活的任何一条伟大的真理。人生原本如此。
那么科学呢?在这里,我必须坦陈我自己的个人兴趣。少年时,我十分热爱自然科学,甚至自制了一个小型望远镜去探索太空。我充满敬畏地渴望了解宇宙更多的奥秘。高中时,我继续钻研科学,后来考取牛津大学,获得了化学学士学位,并开始研究分子生物学(molecular biology)。我曾一度相信科学(当然我还会一如既往地热爱科学)可以帮助我找到生命的全部答案。
但我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然后我意识到,这永无可能。科学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整个宇宙系统中隐藏的原理,但这并不等于告诉我们宇宙为什么存在或我们在宇宙中的地位。虽然理查德-道金斯和我在很多问题上意见相左,但我完全赞同他的“科学无法决定什么是道德的”这一言论。意义和价值是无法从世界中读取的。科学善于将事物进行切分,但分析(analysis)本身是不够的,如何处理这些割裂的部分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需要运用综合(synthesis)来统观全景。科学将事物进行拆分,有助于我们看到其运作过程;而信仰将事物重新组合,使我们看到其意义所在。
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认为,20世纪早期的西方文化逐渐沉迷于他所谓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一些颇具影响力的声音宣称一切都需要加以证明,而科学是证明事物的最佳方法。韦伯无法苟同这类观点。难道不是只有小孩子才以为自然科学可以回答人生的意义与目的这类大问题吗?韦伯语带讽刺地评价那些成年人,他们对科学的思考还局限于青少年的思维方式,而这已经毫无立足之地:
除了那些“老稚童”(在自然科学界的确可以找到这类人)以外,今天还有谁会相信,来自天文学、生物学、物理学或化学的发现可以带来对世界意义的认知呢?@6
韦伯对此还有更深层的担忧。过分强调人的理性,实际上将人们困在了理性的“铁笼”内。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允许自己被理性所监禁,因为他们只能接受可证明的事物。韦伯认为,这直接导致我们对现实的认识非常局限且并不充分。人类需要从理性主义铸造的牢笼中解放出来。
今天仍然有人声称自己被理性所“引导”,实则是被理性所辖制了。他们不顾一切地将现实局限在一个理性可以证明的局促且沉闷的空间中。
在我还信奉无神论时,我曾试想自己的无神论思想是一种勇于反抗的精神,并聊以自慰。人们既然愿意相信如此缺乏吸引力的无神论思想,只能说明它必然是正确的。尽管这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无神世界的单调乏味反而成为我相信自己走上正轨的理由。
事实上,我仅仅瞥见了生命的表层,便断然接受自身认识的局限,拒绝向更深处探索。相信“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成为了智性上懒惰和抱残守缺的借口。这就好比眺望大海中的环礁湖,看到的不过是广袤的蓝绿色水面。然而此时此刻,有人却在海底潜水,从珊瑚礁和穿梭其中的色彩缤纷的奇异鱼群中体会无限的乐趣。它们虽然无法从表面看到,却真实存在着,等着我们去发现。
老套的理性主义将现实局限在可以被逻辑和数学证明的范围内,难怪近年来举步维艰。如今,大多数人倾向于将理性划分为“肤浅的”和“稳重的”两种。“肤浅的”理性将认知局限于可以用抽象的逻辑和数学证明的范围内;而“稳重的”理性承认人类拥有的许多合理观念无法用严格的逻辑证明。“我们的许多观念都没有无懈可击的理性支撑,但它们却合情合理。”(特里-伊格尔顿)
试想你在看过照片上美丽的山谷之后,就知道自己想居住其间。如果理解得当,这便是理性向我们敞开大门得以进入的世界。应用于信仰层面,理性有助于我们认识那可以诠释世界和生命意义的“全景”。这意味着我们无需天马行空地想象某些东西是真实的,或飞奔着投入一个我们为了应对艰难生活而臆想出来、其实本不存在的上帝的怀抱!相反,我们可以通过深思熟虑的论据、跟随内心深处的直觉突破想象力的限制,从而接受信仰。我们当中有些人在追求个人内心安定和自身价值的过程中来到上帝面前,有些人是被上帝的纯然美善所吸引。这些进路都是合理的,它们就像一根根毛线编织在一整张信仰的挂毯上。
当C.S.路易斯抛弃了无神论者早期的“巧舌如簧却肤浅的理性主义”吋,他发现了信仰的丰盛。纯粹理性给他提供的是一个荒凉单调的智性世界,使其无处安身。理性竭力告诉他,除此以外,其他都是纯粹的幻想。而想象力却告诉他,应该不止于此。“几乎一切我所喜爱的,我都认为是虚构的;几乎一切我认为是真实的,却都如此冷酷沉闷、毫无意义。”最终,路易斯发现了一种可以将理性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又可使他与上帝重新联结的思维方式。
这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会在下面更深入地探讨。
寻找全景
路易斯在青少年时期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常常“用一个十七岁孩子的理性主义单枪匹马地炮轰”他的基督徒朋友们。9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更强化了他激进的无神论思想。1918年4月,他在率领步兵发动攻击时受伤。这一时期,路易斯的诗歌作品充满了对这位默不作声、毫不关心人间苦难的上帝的愤怒。战争结束后,路易斯赴牛津大学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先是学习古代思想与文学,后来转到英国文学。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早期的思维模式,曾以为简单朴素,实为肤浅无知。阅读西方文学经典名著将他眼中封闭式的问题重新打开。路易斯在其自传《惊悦》(Surprised by Joy)中写道:“年轻人如果想做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就不能对阅读太过认真,因为陷阱无处不在。路易斯完全不想相信上帝,但最终他发现自己不得不相信。作为“最不情愿的归信者”,路易斯转而探索和解释:使得基督教如此令人信服又能带给人如此彻底改变的是什么。
许多人都认为路易斯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颖悟绝人、发人深省且引人入胜的阐释。那么,他的解释为何如此吸引人呢?他的牛津同事、杰出的宗教哲学家奥斯丁-法雷尔(Austin Farrer,1904-1968)给出了确切的答案。他评价说,路易斯让我们“以为在听他论证”,实际上却“给了我们一个图景,正是这个图景令人心悦诚服”。@11
我理解法雷尔的意思。几年前,我在阿姆斯特丹参加一个会议,其间有足够的闲暇参观美术馆。我最终选择了梵高博物馆,愉快地在画廊中闲逛。我不时地在那些引人注目的画作前驻足,例如梵高1890年的作品《麦田群鸦》(Wheatfield with Crows)。我被这幅画吸引,并试着从多个角度来欣赏。我欣赏梵高的笔触和他驾驭丰富颜料的能力,但吸引我走近这幅画的真正原因,是它的整体图案、颜色和纹理的组合。因为喜欢这幅画,所以我希望更多地了解它。但时间有限,我只能匆匆略过那些无法带给我同样震撼力的作品。只有梵高的画作吸引我驻足探究。
路易斯被基督教所吸引,并非仅凭几条支持基督教的论据,而是因着令人叹服的有关现实景象的“全景”。基督教赋予了一切他认为重要的事物以意义,并回应了他内心深处对真善美的向往。路易斯回忆说,他的无神论思想引出的结论是,他所喜爱、所珍视的一切都应当被弃绝,因为它们都是“虚构的”。然而武断的无神论思想允许他相信的内容,本身却“冷酷沉闷且毫无意义”。这真是令人心碎。然而,基督徒看待事物的方式重新点燃了他的希望,使他所珍视的一切变得有意义。这也肯定了他的希冀与渴望是真实且重要的。随着拼图中的各个拼块各归其位,路易斯意识到,他正在探索的这个信仰世界注定是他的栖身之所。
多数自然科学家都会欣然接受路易斯的方式,因为这与他们的方法论高度一致。一个理论的好坏有待观察来检验,也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解释我们的外在所见和内在经历。当然,好的理论也可能有局限,有时也会含糊不清。但无论如何,好的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人们倾向于被那些富有启发性的思维方式所吸引。
试以侦探剧和犯罪推理小说为例。伟大的侦探小说家都会通过破解其一手炮制出的谜题吊足读者的胃口。作者提供的每一条线索都不足以独立破案,但当这些线索被综合分析考量,它们便累积起来一起指向谜底。也许这些线索不足以绝对证实谜底,但必定有一个最佳答案。我们或许通过自然界的有序和内心深处的直觉便可认出上帝的指纹,意识到这些线索交织在一起是为了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画面。
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1891-1976)对科学方法的哲学内涵及其重要性作出了最具洞察力的一种阐释(科学方法可以被定义为“科学家借以认识世界的合乎逻辑和理性的秩序步骤”)。波兰尼认为,非常清楚,“追求重大发现的动力源于感受到隐藏现实的存在,种种迹象表明存在着一个隐藏的现实”。”波兰尼的见解很容易从科学史角度加以阐释。举例来说,艾萨克・牛顿(Isaac Newton,1643-1727)认识到地面物体的运动(例如苹果从树上坠落)和行星围绕太阳的运动背后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隐藏的现实”。
牛顿称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藏的现实为“地心引力”。对于这个理论,起初他并不确信;但比起他能想到的其他观点,这个理论能更好地解释他观察到的现象。最终,他相信其正确性。这个理论的解释力表明其真实性。他生动地描绘出一个超越人类认知范围的更伟大的现实:
我不过像一个在海边玩耍的孩子,不时地为发现特别美丽的一颗鹅卵石或一个贝壳而沾沾自喜,至于展现在面前的浩翰的真理海洋,我却浑然无知。
许多人和牛顿一样,渴望见到真理的海洋并测量它有多深。借用我们之前的类比,许多人都在寻找一个可以将毛线(即我们的经历)编织在一起,并揭示出人类在宇宙、文化和历史中地位的可靠“全景”。
面对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常常感到不知所措,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去了解和吸收。它只是一大堆事实?或是一连串随机的信息碎片?还是有什么力量将它整合并连接在一起?瑞士神学家埃米尔-布龙纳(Emil Brunner,1889-1966)描写过从苏黎世附近的山上眺望该城的情景。那个夜晚,他看到山脚下闪烁着一片浩瀚的、看似随意设计的灯海;事实上,城市的专业电工完全掌握灯光的布局。他们拥有可以解释当前情况的设计图。
基督教信仰帮助我们在一个表面混沌的世界中看到图案,在别人听到噪音时感受到旋律。它使我们不至于被信息淹没,而是能识别其意义。美国诗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 Vincent Millay,1892-1950)将人类对意义的普遍追寻描述为理解从天而降的“流星雨般的事实”。这些“事实”就像一个拼图游戏中的拼块,只有被拼组在一起,才能展现基督教信仰的全景,这是我们理解事物的框架和行出使命的基础。无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一幅“全景”。只是有些人的“全景”非常狭窄,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那样-将现实局限在冰冷的逻辑范畴之内。
回看一下犯罪推理小说或许有帮助。想象你正在读一本侦探小说,也许是一篇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的悬疑故事。在最后一幕的大结局中,赫尔克里-波洛或马普尔小姐将所有犯罪嫌疑人召聚在一起。接着,大侦探将线索串联起来,描述了可以解释各个线索的“全景”。赫尔克里-波洛讲述了导致这起东方快车谋杀案发生的背后故事,而马普尔小姐则梳理了藏书室中出现一具神秘尸体的原因。事件的“全景”不仅帮助我们找到凶手,还为我们理清了所有线索,就像把线织成了布匹。之前毫无头绪的事件,一旦从正确的角度看待便有了意义。
为了强调把握“全景”的重要性,需要讨论人类内心深处的两种直觉——心灵的渴望和道德责任感,并思考它们是如何与基督教看待事物的方式相吻合的。
心灵的渴望
有一位朋友几年前离开英国,赴美工作。尽管他喜欢那里的生活,但一直没有定居下来。在他内心深处有个声音不停地轻声回响:“你不属于这里,这里不是你的归宿。”他一直无法忘怀自己的家乡。虽然理性告诉他在美国可以过得更好,但内心却另有一个声音。最终,他还是搬回了伦敦。
基督教信仰表达了“这世界并非我们真正的家乡”这一核心主题。我们置身世间是有原因、有使命的。正如迦太基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Carthage,这名基督教的主教因为他的信仰在公元258年被罗马当局处决)宣告的那样,“天堂才是我们的家乡”。保罗也提醒生活在罗马殖民地腓立比的基督徒,“我们是天上的国民”(腓3:20)。我们走在人生的旅途上,尽己所能使其更美好,与此同时,却深知自己属于另一个家乡。心之所系,家之所在;我们的心渴望与上帝同在。
假设我们被造是为了发现上帝、爱上帝,我们内心对上帝存在某种“归巢本能”(homing instinct)。如果我们的被造的确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这如何体现在现世的人类认知中呢?我们可以预见——其实是预测——某种躁动感,反映出我们并不真正属于这里。公元400年左右,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在他的祷文中较好地表达了这一主题:“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缘故而造了我们,我们的心若不在你里面得安息,便不会安宁。”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真正满足我们,那是因为在心灵深处,我们知道内心的渴望根植于别处。
这种对某种超出人类经验范围之事物的渴望,是西方文学不变的主题。德国浪漫主义作家诉说的渴望(Sehnsucht),被诗人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描述为”惆怅而轻柔、饱含泪水的渴望”。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yevsky,1821-1881)表达了自己在“心之梦想与灵之遐想”中感受到的“无边的忧烦,有时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经验。20世纪最有口才且最具影响力的英国无神论作家之一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在1916年时写道:
我的内心不断陷入到一种极度痛苦的状态中……寻找一种超越世界的东西,那美好而无限之物一上帝这一荣福美景,我没有看见,也不认为它可以寻见。但是它的爱就是我的生命……它是我里面真正的生命源泉。
罗素的女儿凯瑟琳-泰特(Katharine Tait)回忆说,父亲之所以藐视有组织的宗教,对宗教观点不予理会,主要是因为他不喜欢持有这些观点的人。但泰特认为她的父亲毕其一生其实都在寻找上帝。“在我父亲脑海的某个隐密处,在他的内心与灵魂深处,有一处空白曾经被上帝填满,从那以后,他再也找不到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将其填满。罗素有着某种“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幽灵般的感觉”。
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体验——一种强烈的属于另一个地方的感受。总有些事物更加美好、超出我们的认知吗?这样想是否意味着我们是这场毫无意义的骗局的受害者呢?抑或它是一个线索,引导我们发现生命的意义和我们在这个宏伟计划中的角色?
路易斯为解开这个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在皈依基督之前曾经有很多年承受着这种神圣的不安(divine restlessness)。路易斯指出,大多数人都在渴望某种东西,当他们真正得到时,却感到失望而沮丧。“我们在最初渴望之时捕捉到的某个东西在现实中消逝了。”
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1882-1941)对此深有体会。她称之为“存在的瞬间”——短促而直刺人心的豁然醒悟,似乎在向她揭示“表象背后某种真实的东西”。“这些难得的稍纵即逝的“瞬间”使她相信,在已知世界的背后,隐藏着意义与联系的巨网。但她永远无法进入这个隐藏的世界;每当她靠近时,那扇门便隐退了。
你也许同样站在一个通往深邃意义的入口处,却发现随着顿悟的瞬间消散而被拒之门外。我们被“总有某种存在”的强烈感受所困扰,但顽梗的理性主义者可能视之为迷信的胡言乱语,对其嗤之以鼻。
这种经验的意义缘何如此难以把握?路易斯认为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是我们正在错误的地方寻找意义;其二是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可寻;第三种更有帮助的解释是,我们可以将尘世的渴望当作是我们真实渴望的“摹本、回声或影子”。它们是从我们真正的故乡中射出的“快乐之箭”,旨在唤醒我们沉睡的心灵。没有一种尘世的快乐可以满足我们不断膨胀的欲望,它们原本也不是用于满足这些欲望。那只是为了唤醒我们,暗示我们去寻找某种真实的东西,令我们坐立不安,直至寻找到源头。“有吋是希望为真理插上了翅膀,有时是真理放飞了希望。”
人际关系可以营造出一种对某些事物悲喜交加的渴望——这些事物来自于关系,但不存在于关系之中。这一主题反复出现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伊夫林-沃(Evelyn Waugh)的著名小说《旧地重游》(Brideshead Revisited,1945)通过主人公厌世的上尉查尔斯-赖德的经历,向我们传递了许多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的挫折。在他“神圣和亵渎的回忆”中,一开始他只是一个“寻找爱”的学生;到最后却落得“无家可归,无儿无女,人到中年,没有爱情”,他苦思冥想自己的追寻为何注定是一场空。
快乐、美丽、人际关系:一切看起来都充满希望。可是每当我们努力抓住它们时,就会发现寻找的东西根本不在其中。路易斯指出,我们——就像他所经历的——会逐渐意识到,“我若发现自己心中的渴望是此世任何经验都无法满足的,那么最可能的解释是,我是为了另一个世界而造”。正如肉体的饥渴指向可以被食物满足的实际需要,精神的饥渴则对应于可以被上帝满足的实际需要。
当然,这个观点并不能证明基督教是正确的.也不能证明上帝的存在。但这不是路易斯想要表达的观点。他想论证的是这个解释与我们的经验相符,与“全景”相一致,也可以用全景加以阐释。
让我们来看看基督教的全景如何与人类经验的第二个方面相吻合。
道德责任感
正常人很难不去思想各种行为的是非对错。但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理查德-道金斯所相信的“善”是人类的发明这一观点正确,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事实——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所言:“我们内心深处除了自己放置的东西以外,原本一无所有。”一旦我们决定什么是对的,就要决定什么是错的。如果世间不存在绝对的真理,我们就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正确的,那么道德便沦为个人偏好的问题。
难怪罗蒂对自己的结论深感不安。若不诉诸超越人类文明的权威,当“施刑者残害无辜”时,他将如何应答?不过,他坚持认为,事物本身就是这样。他的同事和学生对此持有异议,时常挑战他的观点。到最后,罗蒂干脆拒绝谈论他的观点。但是逃之夭夭是无济于事的。
假设对与错只是个人选择的问题——是我们发明的东西,那么难道喜欢自由胜于压迫,就像喜欢巧克力胜于香草冰淇淋一样,只是个人偏好问题?若在我们看来完全是误入歧途的事情,当事人却心安理得,怎么办?纳粹德国似乎认为灭绝犹太人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好在其他人认为这种做法当受谴责。道德相对主义之所以(该观点认为不存在判定事物优劣的客观道德价值标准)土崩瓦解,是因为它无法为其基本观点提供有力的支撑。“这是好的”,沦落为“我喜欢这个”,或“我的朋友和我喜欢这个”。于是司法沦为权势的附庸,相关利益集团的主张得以执行。
这一点十分关键。即便最顽固的道德相对主义者为“做自己喜欢的事”辩护时,也会遇到麻烦。没有谁把这种观点当真。路易斯指出,我们都知道有高于我们的存在个人们可以诉诸、也希望他人遵守的规范;“一个真实的法则,这个法则不由我们发明,我们却知道自己必须服从它。”
这也不只是个人问题。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的道德相对主义使他能够在意大利建立起法西斯专政。那个年代崇尚“一切意识形态都具有同等价值”,因为它们都是“纯粹虚构的”,因此无论你相信哪一个都无关紧要。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意识形态,并尽其所能贯彻执行”。墨索里尼做出的判断是,他的法西斯意识形态将在意大利大获全胜,因为那时的文化观点(cultural outlook)将一切严正批判墨索里尼的思想全部推翻,而后来也的确如此发生了。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与人们心灵深处的直觉存在巨大的割裂。如果宇宙结构中并没有“自然公义”(natural justice),何以阻止社会权力组织将其自身的是非标准强加于人?如果不存在超越人类的力量使这些人对自己的观点和行为负责,我们如何能抵挡他们呢?
许多世俗伦理思想家也认识到这一点。比如英裔爱尔兰哲学家艾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认为,人们不得不相信“作为道德人,我们置身于一个超越自身的现实中,道德进步意味着认识这一现实并服从它的旨意柏拉图认为,人类的正义观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超验的、不为人类所操纵或控制的正义观的回声。对默多克而言,对超验正义观的信念是避免让“对错”沦为社会强权者之专断臆见的唯一途径。如果有权有势者为了成为赢家而操控一切并随意修改规则,那一定是错误的。
诗人奥登(W.H.Auden,1907-1973)在1939年发表了著名诗歌《停止所有时钟》(Stop all the Clocks)。次年,他抵达纽约,得出了以上结论。奥登在20世纪20年代初放弃了宗教信仰,取而代之以含糊的左翼观点,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以及人类理性解决危机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不久,他在曼哈顿德裔区的电影院观看了一部新闻纪录片,该片讲述纳粹攻打波兰。令他震惊的是,观众席中那些“很平常、不伤害他人的德国人”开始叫喊“杀死波兰人!”
震惊之余,他不再相信人性本善。但若要说某些事绝对邪恶,必须有绝对的标准来支撑这一判断。随着奥登对该判断的深入体悟,他意识到自由主义其实是作茧自缚:“自由主义思想一直以来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侵蚀对绝对标准的信心。”奥登重新拾回了对上帝的信仰,这源于他认识到“绝对”的重要性,以及基督教的“全景”与之相合并有维护“绝对”的能力。
奥登和很多人都意识到,基督教的思维方式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类难题并找到解决方案。即使人们在理解和实践中屡屡失败,上帝还是公义最根本的基础和保障。我们内心深处的道德责任感是上帝的指纹,反映出上帝更新被造物的愿景,而且也邀请我们参与并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在此重审,这并不能证明基督教是正确的,只是提供又一例证,说明基督教的理解框架与我们的日常经历和心灵深处的直觉相吻合。
开拓视野
我们之前一直在探讨这一观点——基督教使人看到全景;它开拓了我们的人生视野,使我们领会到现实的深度,不再将视野局限于可“证明”的有限地带。哲学最确定的结论之一即理性是有限的,逻辑和科学亦如此。我们知道这三门学科有助于人们避免犯错。但是,知道无法画出六边三角形与解答人生至关重要的问题还相去甚远。它无法帮助我们寻见——更别说真正明白——充满意义之人生的核心:真、善、美。
我们之前提到过,那个超越理性的世界布满暗示与线索,敞开大门邀请我们去探索并栖身其中。我们或在宁静时分听到过阵阵旋律,或在凉爽的傍晚闻到缕缕幽香,或听闻那些踏上过这片土地的人分享他们的奇遇经历。这些“超验之迹象”(signals of transcendence)鼓励我们相信,在日常经验之外还有更广阔的存在。正如G.K.切斯特顿所言,人类的想象力超越了理性边界,“真正的艺术家”都认为“自己在触摸超验真理;而他的画像是透过面纱所见事物的影子”。”
想象有人在一座岛屿的海滩上漫步。一天,他沿着海岸线散步时,发现有东西被潮水冲过来。那是一种奇怪的植物,与他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他十分不解地摇头,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岛上从未生长过类似的植物啊。于是他意识到这可能来自他视线之外的土地,被洋流带到这里。他才知道世界比他想象的更大。
尽管超验之迹象与神圣之音的回声令我们大胆猜想,在现代世俗主义的萧瑟风景之外别有洞天,但它们本身若孤立存在便毫无意义。基督教的全景赋予了它们意义。
那位将线索植入创造秩序的上帝并没有无所事事,等待我们去注意他。上帝选择对我们说话,并主动来寻找我们。有的哲学家断言理性只能将上帝归结为宇宙的某种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 of the universe)。然而,我们必须坚持上帝不能这样被理性所局限。没有一条合理的哲学推断能够否认存在一位对人说话的上帝,而这位上帝——用人所能理解的话说——想要被人认识。基督徒看待上帝的视角与理性并不矛盾,它只是拓展和丰富了理性,突破了想当然认为的华而不实和肤浅之理性主义的局限。
为了深入探讨这一点,我借用一个熟悉的比喻,这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经典作品中可以找到。柏拉图让我们想象有这样一群人,一生受困于一个地下洞穴。一团燃烧的火焰将摇曳的影像投射在洞穴的墙壁上。这群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这个洞穴是他们所经历的唯一的实际。他们没有任何参照物,在他们眼中,这就是世界的全部。读者当然清楚,有更大的世界等待他们去发现。
第一次阅读柏拉图的这段文字所带来的感受令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高中最后一年,我准备升入牛津大学深入学习自然科学。那时,我仿佛悠然自得地倚在一个新奇美好的世界边缘,满怀期待去证实我那尚未成熟的无神论思想,并为它提供新的智性活力(intellectual resilience)。当读到柏拉图的这个比喻时,我里面那个铁石心肠的理性主义者轻蔑地笑了。典型的逃避现实的迷信!所见即所得,仅此而已。然而一个微小的声音嗫嚅着发出疑问:如果这个世界只是全景的一部分呢?如果这个世界是虚幻的呢?如果在它之外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呢?
假如那时我读过C.S.路易斯的作品,就会知道他也曾经历相同的困惑,并渐渐认识到他青年时期的无神论思想何等缺乏想象力。其实在没有读到路易斯的作品时,怀疑的种子已经播撒在我顽愚的无神论思想里。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的疑虑竟扩大到完全将我征服,并引领我重新认识了基督教。
设想我们从柏拉图的比喻向前迈进一步,提出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洞穴里的人们如何才能察觉现实要比其昏暗拥挤的洞穴大得多?他们的眼中只有这个幽暗阴森、烟气缭绕的世界,何以发现在它之外,另有一片灿烂、明媚、纯净的土地,那里空气清新,花香醉人,色彩艳丽,景致盎然?
这个洞穴里或许有线索暗示在潮湿阴暗的墙壁之外,存在另一个世界。风向正确时,这些地下居民可能会嗅到遥远的花香,或听到潺潺的山泉。他们还可能会在墙壁上发现从未见过的令人费解的雕刻图案。
还有另一种可能。假如有人从外面进入洞穴呢?如果这个人是来解释外面的世界并愿意带他们前往呢?最后,洞穴里的人必须做出决定:是否要相信这个陌生人?是否愿意接受他带领我们走出这个熟悉的洞穴,去一个崭新而神秘的世界?
这些问题在记载拿撒勒人耶稣事工的新约福音书中有所探讨。这个人是谁?他值得信任吗?在我们已知的世界之外,是否存在另一个世界,拿撒勒人耶稣能否带来有关那个世界的信息?或带领我们走进那个世界?难道他只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宗教导师,为我们提供活出美好人生的技巧?还是他能够改变一切,医治那些破碎受伤的人,在死亡面前带给我们希望?
我们将在后面几册书中更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当下,我们将着眼于“全景”——一幅基督教信仰要求我们相信、邀请我们进入,并鼓励我们卸下重负去细细品味的实景。本章已就这一主题进行了多方面讨论。在下一章,我们将依次介绍三个模型和意象,帮助我们进一步发掘这一全景。